 |
李安 Ang LEE
義無反顧的中場戰士 |
2021-12-28 |


李安,導演、編劇。畢業於紐約大學電影製作研究所,以「父親三部曲」在全球打響名號,再以《理性與感性》等片成功叩關好萊塢。曾憑《喜宴》、《色,戒》兩度榮獲金馬獎最佳導演,《斷背山》、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奪下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,更囊括兩座威尼斯影展金獅獎與柏林影展金熊獎,為國際影壇最受推崇的華人導演之一。近年致力於運用前衛的電影科技,探索深層的人性情感,以《雙子殺手》再次挑戰超高規格的電影製作技術,為電影產業敲開未來之窗。

時間:2021年11月25日(四)13:30-17:30
地點:不只是圖書館
講者:李安 Ang LEE
講題:導演/義無反顧的中場戰士
文字記錄:林子翔
攝影:桑道仁

這次我想講的不太一樣,我自己也沒有試過,我想用比較課程的方式來試一試。通常都是大家問我問題,我想到什麼就講什麼,這次我想準備一下。一般講座會講一些比較抽象的東西,這是什麼idea啊,為什麼這樣子做,講我心裡的感受,順便講一些過去的經驗,今天設計成一堂課程,我想講一些比較實際的工作。平常在講座上講的內容,不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在想的事情,我的生活也不是都在處理我的想像,而是去想要怎麼把我的想像印證、把它拍出來,拍出來都是很實際的東西。你們都有拍攝經驗,我想分享一些工作經驗,從你們提出的問題裡拿一些實例,我們準備了一些片段,那為什麼選了這些片段來跟你們分享,因為這些都是過去讓我刻骨銘心、非常痛苦的一些片刻,當時每天都不曉得怎麼過的。
在拍片會碰到各種不同的難題,這些東西對我很重要,因為我碰到特別的困難,它就會刺激我去找出方法。拍片其實是非常珍貴而難得的事情,準備了很多年,至少好幾個月,這麼多人、這麼多因素就在那一天發生,你怎麼樣把它捕捉下來。如果你的計畫或手法不到位,一不小心這些想像就會從你的指縫間溜出去,非常可惜,然後你會後悔莫及。所以我每天想的是怎麼樣讓這些東西不要流失,這些是跟技術(craft)有關係的。我覺得品味、想像是沒有辦法言傳的,每個人想的都是不同的東西,電影是電影,它不是語言,沒辦法言傳,不是一個非常邏輯性的東西。但是你要用邏輯的方法組織大家,放進一個有邏輯性的故事裡面,然後去捕捉你想像的一些潛意識、無意識的東西。那要怎麼抓到就需要技術,技術是可以言傳、可以教、可以分享的。我今天就是想換個方式,不要講那些比較玄的東西,那些在訪問或宣傳的時候我可以講,今天想講的是我做為一個導演每天要面對的事情。這些片段裡面的很多東西,可能是你們已經知道或正在做的事情,可能聽起來會有點煩,不是那麼刺激想像力,不過這是我每天的生活,跟你們分享一下。
《理性與感性》Sense and Sensibility
先講一下我為什麼選擇這些片段.你們看看有什麼問題,我們可以激盪、討論。第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《理性與感性》,這是我記憶中拍得非常痛苦的一次經驗,拍《理性與感性》的時候我的英文講得不太好,可是我要去導英國古典文學,跟英國最優秀的演員與技術人員一起工作,算是大聯盟吧。那時候我拍過三部片,以他們的標準來看是獨立製片的規模。在藝術上我有我的作法,但是在工業體系、電影知識、各方面的規矩等等,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蠻嫩的,語言不通要導英國的電影其實非常害怕。
這大概是第二、三個禮拜吧,非常痛苦。我們在一個英國的歷史古蹟裡拍攝,裡面不能打燈,勘景只能看一下,也不能排戲。這場戲前面是一場沉重的戲,這場就轉換成很輕快的。休葛蘭(Hugh Grant)來看艾瑪湯普森(Emma Thompson),她的心情非常沉重,有一個很沮喪的妹妹凱特溫絲蕾,還有一個像小三的女人在纏著她,其實是很輕鬆、很雋永的一場戲,但是又很沉重。問題是這個空間本來就不大,演員有站有坐,每個人都有一個動機,互相衝擊,每個人的個性又不一樣,演員都是舞台劇或電視出來的,電視出來的演員就很喜歡對著鏡頭表演,舞台劇出來的演員很喜歡走位,喜歡用身體表演,口條也非常快。我計畫了好幾天,分鏡、鏡位都做出來了,到現場一點都用不上,演員一走位我整個腦筋就亂掉了。
拍電影基本上兩種拍法,一種是Assembly,就是你把它連續起來,就是連續性的線性思考。另外一種是Coverage,台灣電影裡面Coverage用得比較少一點,這跟我們的工業、經濟環境有關。Coverage是從各個角度去拍,每個人都cover到,然後到剪接台上再去工作。這種比較需要靠集體的功力,一個人想還不夠,團隊裡面的場記、剪接,剪接點怎麼銜接,演員的素質、訓練都要到位,你才好調動起來。還有鏡位的運用,通常會有幾個key moment,包括攝影機的運動,如果有特別麻煩或是重要的東西,我會先把它定調,中間怎麼走位還必須去變化。我看台灣電影裡,尤其年輕導演常常會比較單純,就是有個目的,然後怎樣去把它做出來;但是你拍這種戲的時候,其實每個角色都有各自的角度,每個人都是很立體的,有自己的目標,相互撞擊之後是很精彩的,很難用導演的單一觀點去整合他們。那時候我英文不好,以我的資歷也叫不動他們,所以我必須要找到一個活路,讓他們去表現。
我本來估計一天要拍完的,但前半天都在流冷汗,拿他們一點辦法都沒有。有的人站,有的人坐,一站起來視角就變了,然後四個演員的走位跑來跑去,我腦筋都打結了轉不過來。等想到差不多的時候,一個演員的位置一動,我想說這樣好像也很好,就又亂掉了。攝影組也搞不定,光一定要打得佷漂亮,然後場景又不准架燈,要架到六呎以外,用室外光源進來,怎麼樣做到漂亮?還有明星的眼神光,這些都要做到某一個程度,不然他們不給你拍。我只有拍三部片的經驗,所以去到那邊真的是啞巴吃黃蓮,大概搞了六個禮拜之後才慢慢磨合。
我對他們的工業體系也不熟,連英語片都沒拍過,我以為是導演、副導、攝影師在場景裡面想怎麼去運作,兩天之後我才發現英國的系統真正在指揮的是掌鏡的那個人,很奇怪的一個系統,但又很合理,因為攝影機是他在操作,他在指揮燈怎麼擺、順序怎麼拍,他最清楚整個流程,每個人就繞著他去調整,看怎麼樣做才順手。而且那些掌鏡的人非常厲害,英國演員有時候會做一些小動作,他要提早四分之一拍到位,那個功夫很厲害,然後他怎麼去cover,我們用了Dance Floor讓攝影機更流暢運動,這是我第一次用,幾個鏡頭可以混在一起,那時候這些東西我都不會用,所以說很多很多東西加進來。用Coverage的好處是你不會一下就把戲拍死,現場某個鏡頭很好,你想像的很好,但整個片子剪起來,可能單一場戲你就把它拍死了,我們話不能說死,拍戲也是一樣。拍攝素材只是採購,真正在做菜是在剪接台上面,所以你要怎麼cover足夠。像這種素質的演員跟工作人員,他們很清楚整個電影規格,比那時候的我清楚得多。這場戲我拍完以後,好像沒有人能夠再唬我,真的是當場鍛鍊,我前半天都在流冷汗,真的不曉得該怎麼辦,腦袋一片空白轉不過來。後來有一件事情讓我茅塞頓開,對我的整個電影生涯影響很大。
我想奉勸你們,電影不管想得多偉大,拍電影不是要把它拍完,而是要拍好,除非你能夠把它切割到你可以掌握的區塊,不然很難拍好。你心裡想得那麼大,但是遇到困難每天生氣,那是不會好的,所以你一定要稍微有點智慧。拍攝現場常常很混亂、很難掌控,在還沒到現場的時候,你就要想好幾個最重要的區塊,把它掌握住,先把錨定下來,比較不會出亂子,然後你才有可能去做即興的表演、做變動,所以你最好能夠區隔。你們等一下看這場戲,其實有一個原則就是「三娘教子」,三個女人在整一個男人。那時候我沒有拍過明星,我只拍過演員,我不曉得休葛蘭的魅力在哪裡,後來發現他是所有女人都想餵他雞湯,讓其他男人嫉妒。這場戲是幾個女人巴在休葛蘭旁邊演戲,那時候凱特溫斯蕾(Kate Winslet)很年輕很熱情,凱特就老是貼著休格蘭,過了半天我才發現休葛蘭好像是希望自己一個人演,所以我想通的是把休葛蘭跟三個女人拆開,之後日子就好過了,我的問題解決一半,果然一拆開大家都乖乖的。
因為艾瑪湯普森是不會動的,她是一個心情沉重的人,她代表的是理性嘛,不管她的角色或是她在電影裡面的心態,她就是不會動的。另外一個小三就是來纏艾瑪,她的目標是休葛蘭,艾瑪不動她也不動,所以我只要處理一個菜鳥就是凱特溫絲蕾,那時候我還可以調度她(笑),她那時候才十九歲,叫她不要過去她就不過去,所以我只要把她拆開,整個就撥雲見月,我就可以開始去調整每一個人的戲,每個鏡頭怎麼樣去做,就可以好好拍戲了。本來是一天拍完,我超時了,我拍了兩天才把它拍下來,可是終於有拍到了,拍得還不錯。這場戲心情沉重,可是它有英國式的幽默,節奏要非常輕快,需要的角度基本上都抓到了,有眼睛的角度,站起來、坐下來的角度,還有攝影機在中間的角度,然後四個角色三條視線,其實我把他們切開之後,四個角度變成兩個角度,那我就比較好控制了。一邊是三個層次的話,我再偶爾加個東西,兩天就混過去了,這部分給我的啟發很大。
不過其實也不一定,有些你朝思暮想的鏡頭拍出來就是線性的,後面會有一些線性的片段。因為有些鏡頭不可能cover,這跟藝術沒有關係,就是那些鏡頭太貴了,像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。像這場純演員的戲,我覺得用cover的方式比較好,你從每一個人的角度或一個主題出發,大、中、小的鏡頭,上、中、下三層,什麼時候該換場,什麼時候是戲劇的重點,戲劇重點也不可能一直持續三、五分鐘,因為它一直在轉換,轉換的時候要用什麼中景或遠景來cover。這些定出來以後,其他的就可以再去發展,你才會有真正的自由,才會有真的手法去經歷,才有能力去控制。
導演一旦慌了就很糟糕,拍獨立製片可能還好一點,碰到這種工業的作品,製作稍微大一點,大家看你在那邊流冷汗,大家問你問題,你一下講這個、一下講那個,抓不到重心,非常難看,人心渙散一塌糊塗,像骨牌一樣,所以中心思想ㄧ定要先把握住。怎麼把握呢?第一個就是一定要有中心思想,如果沒有中心思想,拍出來就是很匠氣的東西。最主要的精髓是什麼?這場戲需要把握什麼?就像我想到的三娘教子, 別的導演可能看不到三娘教子,那這就是我的風格。你都掌握住每個人的個性、對比,如果你連這個都掌握不到,你就沒有辦法指導大家。這個掌握住以後,你就先動動腦筋,因為像這種戲大概都是要當場排,排了之後分鏡,寫下去之後大家才知道整天的工作流程,所以你要很積極,要準備充足。
主旨是什麼?主要的元素是什麼?幾個重要的轉景或是一定要捕捉的場面是什麼?都掌握了以後,就可以隨便演員跑,訂出了主題架構,演員怎麼跑都跑不掉,因為演員不可能跑出素材之外。如果他亂跑的話,你就可以教訓他,如果人家講的有道理你不聽,那真的就是你不對。你都抓到之後再去調細節,可能再加入一些做不到的、比較抽象的東西,這時候就比較好做。如果全部都是抽象的話恐怕會很亂。那我們來看看片段,看了之後你們有什麼問題我們可以來討論。(播放《理性與感性》休格蘭拜訪艾瑪湯普遜片段)
對我來說,有些大場面的戲看起來很難其實很好拍,像這種戲反而比較花腦筋、比較耗時。因為它的角度很多,每個人都有他的歷史,每個人都有他的表情,你能夠捕捉到就能夠帶領觀眾往那個方向去想。不是你拍了之後讓大家去猜,猜也有一個範圍。非常花腦筋的一場戲。有沒有什麼問題?
Q:剛剛導演說本來拍一天變兩天,那製片有給你壓力嗎?
李安:一個壓力就是錢,像這種一天就要花很多錢,再來就是場景的壓力,這場戲拍一天,第二天本來應該到其他地方,包括人員、演員檔期、場地等都要重新安排。有些場景可以移動,譬如說這個房子總共拍幾天,可以稍微移動一點。像這個房間只有一場戲,第二天本來要到另外一個地方怎麼辦?他們拍戲都幾十輛卡車,動作很大,所以它牽扯的因素很多,包括金錢、調度、壓力很大。還有就是我一個外國人去那邊導英國文學,別人看你好像不會拍片,對你沒有信心,這其實是最大的壓力。錢財或其他東西都是可以處理的,可是對你沒有信心,尤其是在一開始,對一個導演來說,這是非常巨大的一個壓力。我現在比較好了,拍了那麼多部片,大家知道我不是故意刁難或是不會拍,我可以比較從容地去解決這些問題。
但那時候是我第一部英文電影,飄洋過海、猛龍過江,就我一個人,美國人就一個或兩個,講中文的更是一個都沒有,其他全部都是英國人,那個心理壓力很大,我想那時候就是被嚇到了。如果導演碰到這個狀況也沒有辦法,只好自己克服。我希望那時候有人可以跟我講說:你可以切割ㄧ下,把範圍縮小,可是沒有人告訴我。這是我們的美國製片企劃出來的劇本,可是他也沒有拍過片,所以我身旁沒有一個有經驗的製片可以帶領我、安慰我。大家眼睛都瞪著你,我英文又不太會講,只會蹦幾個字出來。其實這都二十五年前了,我想最大的還是心理壓力,做為一個導演,我可以告訴你們的是,如果心理因素能夠減少一些,其實很多事情都想得出解決辦法,如果你被嚇到,心裡一矇的時候就很糟糕,整個信心垮掉,這對片子很不好。
Q:第一天拍完拖到進度了,之後跟製片協調的過程是什麼?
李安:大概到早上十點鐘,不需要製片來說,大家就知道你拍不完了,製片就會商量拍不完該怎麼辦。原先你跟他們講大概多少個鏡頭,拍這麼慢,給你一天還拍不完,其實大家就曉得的,都很有經驗。我有碰到相反的例子,像在洛杉磯拍《綠巨人浩克》,到現在這還是我拍過最貴的一部電影,那個就無法無天了。我常常看到製片在商量,我問他們在商量什麼,他說如果這個拍不完我們該怎麼做,我說拍得完啊,你告訴我幾點要拍完,我就幾點把它拍完,然後我就真的把它拍完了。我說你為什麼不告訴我,他說不敢逼我。這就是一個相反的例子,但《理性與感性》的時候沒有,那是很大的壓力,我想拍台灣電影會比較少遇到。
之前我在台北拍《飲食男女》,那時候就拍到十八個鐘頭,大家都是在睡覺,要把人家搖醒繼續工作,現場錄音都是打呼聲,然後回家睡了十個鐘頭以後繼續拍,沒日沒夜的。也沒有人計劃,有計劃也沒有人聽你的,那時候拍戲就這樣,也是另外一種拍法。那就磨嘛,一個鏡頭、一個鏡頭慢慢磨,也無所謂Coverage還是Assembly,想到什麼就拍什麼,也沒有人逼你。我不曉得那部片拍了多少錢,總之總有一天會拍完。到了我最近這幾部,譬如拍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,一天什麼都不拍,光是人湊齊就要四十萬美金的基本費用,那是很大的責任。四十萬美金都可以拍兩部台灣電影了吧,我們一天什麼都不做就有那麼多錢在燒,那是很大的壓力。拍那個水戲,有時候一整個晚上都拍不到,真的要哭出來,那些都是很貴的戲。我是覺得能夠減少就盡量減少,不要因爲人為因素讓你犯錯,做不到藝術的要求,有時候你帶了幾百個人甚至上千人在拍的時候,最好把它歸納到一個範圍裡面再去做調整,我覺得這是有幫助的。
Q:《理性與感性》這段您是用Coverage拍攝,關於分鏡的分配,您會請演員只演某個特寫或某個中景嗎?還是你會請他演更長的段落?
李安:通常工作人員也會幫你,角度相近的鏡頭,有可能會歸納在一起拍,不然調度的時候,整個燈、布置都要重來。十個鏡頭可能只要六個就可以拍下來了,所以我們就是鏡頭分出來之後也會再歸納。在分鏡頭的時候,我的腦筋也會稍微過一下,拍這麼多年了,尤其這部片之後經驗更多了,我都會在腦中整理一下,我大概會知道一天拍得完還是拍不完,所以像這種情形以後就很少再遇到了。通常我會整理一下,大家也會幫我整理,你會發覺沒有想像的那麼糟糕,有些鏡頭可以合併組合,譬如說兩個鏡頭角度差不多,調一下就算成同一個。
還有幾個太麻煩的鏡頭,就像你看到Dance Floor,我用了好幾次,演員要走位的話,鏡頭完全切開也很死板,或是分的鏡頭太碎了,那攝影機就要搖一下去捕捉,如果搖的時機不好,在剪接台不好剪的時候,你還要留一手對不對?所以可能另外的角度就要cover一下,這才不會說鏡頭現場看很流暢,剪接的時候卻剪不通,有窒礙的話你就要有別的角度去cover。所以cover跟cut away(切出鏡頭鏡頭),cut away就是切到其他地方,這些都是很有用的東西,你不見得當場有用,但是將來有可能用得到,就先把它放在手上。
更早以前像約翰福特(John Ford),那時候導演沒有剪接權,他們就是去拍,也不寫劇本,也不剪接或宣傳,一年拍四、五部,也都是經典,送去給誰剪,剪出來都一樣,這就是Assembly的拍法,當然他的腦筋是很清楚的,大師沒話說。你有Coverage,製片、老闆就有可能管到你,因為他們也懂這個東西,就是自己要衡量,有時候我很堅持要一個東西的話,我就不會拍Coverage給他們。那時候我還拗不過人家,有一場休葛蘭跟艾瑪湯普森的戲,我就是用台灣拍法,兩個人面對面坐,整場戲從頭到尾都不動的長鏡頭。但是一開始的時候做不通,因為演員也不答應,他們想要別的演法,跟片廠也講不通,還好我的總製片薛尼波拉克(Sydney Pollack),他是很有名的大導演,他就幫我去遊說,說只有英國演員才能這樣從頭到尾一動都不動,美國演員就做不到,後來就成功拍攝了。
現在我可以講這種話,可是那個時候我還沒到那個份量,現在我有可能就直接這樣拍,就不給你Coverage,那是一種不太合理的態度,有時候要耍一下性格的話就這樣弄。可是做為一個職業拍電影的人,要跟老闆、演員合作,拍Coverage是你的本分,但要精簡、要合理,也有的大導演什麼都cover,那也很浪費錢,剪接師無所適從,不知道怎麼剪,我覺得這也有一點浪費時間,一般片廠是任何可能的coverge都希望要做到,我覺得這個也不足為訓,就變成什麼人都可以拍,那要導演做什麼呢?所以說還是要堅持,你特別想要的鏡頭要堅持一下,或是你在做遊走或串連,把五個鏡頭變成一個鏡頭,那是好的,因為如果沒有這種鏡頭的話,電影看起來會很死,就跟電視片一樣,不過演員是喜歡這樣的,因為他知道攝影機在哪裡,他很好演,這些人都很精,到現場都知道狀況。
等一下有一場戲,我把攝影機們擺一個方式,讓演員不曉得要往哪裡演,你跟演員有鬥爭,但也有合作,不管怎樣都好,總之大部分要合理。如果每個鏡頭都在搞怪,就很難做下去,很難跟人家合作。拍很小的片子可以,可是稍微有點規模或有明星的時候就不行,很難做得通。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基本功,你不一定要用,但你要懂,口袋裡要有這些東西。對我來說有些角度是非要不可的,其他的你要懂怎麼cover。
每個演員都需要表演,你都讓他有機會表演,滿足之後他就很乖像小孩一樣,乖了以後你說能不能試試別的方法,他也會很合作,不會說你把他拍成不想要的樣子,然後就開始抗爭搞怪,跑來跑去。我剛開始拍的時候,他們就是跑來跑去,就是不滿足。他們演到滿足之後,你就再做其他要求。一般的演員都是這樣,有時候要順著他們,但有時候他們也希望你逆著他們一些,表示你有個性比較特殊,就看你怎麼運用。若是時間趕,今天不拍到的話,不可能過兩個月再回來拍,那就算戲拍差一點,你還是要把它拍完,這種方法也要有,安全網的東西你也要會,有時候沒辦法嘛。像我到哥倫比亞拍《雙子殺手》,那個城牆四百年了,只有那天他們准你上去拍攝,還有觀光客、文物保險的一堆規矩,拍不完就拍不完,那是你家的事情,導演就是要很有紀律、很有計畫,要有變通的方法,要想拍不到怎麼補救,這都是很切實的拍片生活吧。
Q:請問導演,這場戲你會讓演員全部排一次,再讓攝影師去拍嗎?
李安:我會對過台詞,在開拍前排演的時候會對過,可是我覺得電影的排戲不像舞台劇,不需要排練精緻到他可以自己上場去演整場,都不需要導演。拍電影最需要的就是拍攝當天怎麼去捕捉,所以排練也不可能排得很好,其實就是每個人的個性、動機,彼此的化學作用,他們大概有一點印象我就打住,不要排得太細。我們當導演就像是當一個教練,如果是籃球教練,在練習的時候,我不會讓選手把力氣用光,最好的要留到比賽的時候,那拍電影就像是比賽,排練大概抓到那個味道,讓大家有點概念,我通常就收了,不可能排到很精細,精細的東西通常都是當天到現場再去排。
我會慌亂也是因為都是現場排,服裝、頭髮、一堆東西,這些你不在現場看就很難計劃,所以就是現場排,化妝差不多就來排戲,排完戲之後他們再去化後半段的妝。我們就接著來分鏡,分完鏡,打字出來送給每個部門,他們就知道要準備什麼道具,燈光怎麼打,走位怎麼走,這些就讓副導跟攝影師還有大家商量,這時候我的工作就比較輕鬆了,我只要去挑一下毛病,演員表演後去調整,所以早上去排戲和分鏡是最有挑戰性的時候。
Q:請問導演,你身為一個外國導演去拍這種英國古典文學,怎麼去說服資方?
李安:是他們找我的。其實我後來才知道他們找不到好的英國導演,因為他們從小看膩了,所以開始找外國導演。美國人也不願意導,版權所有者是大導演薛尼波拉克,他說他是從俄亥俄州來的怎麼會懂英國文學,那台灣人就懂嘛(笑)?所以他也不導。還有一個蠻有名的英國導演麥克紐威(Mike Newell),執導過《妳是我今生的新娘》,他說「我好心告訴你,這個片子最糟的就是找英國導演」。所以他們就開始找外國導演。我是他們找的人裡面唯一提到珍奧斯汀(Jane Austin)的幽默感的人,那我有跟他們講到幽默,還有一些感情戲,他們覺得很受用。他們是看了《喜宴》之後覺得我可以導,雖然我在文化、語言上比較吃虧,可是我可以拍電影。
我之前三部都是拍家庭劇,這些東西原則上我都懂,只是沒有用英文、用古裝戲去做過,也沒有跟這些人合作過,這是我的挑戰。其實這裡面的味道我已經很熟了,他們看得出來。不過那個時候很困難,對他們來說是很大挑戰,現在大家合作慣了,像你們這代大概不會有這個問題,那個時候沒有辦法想像怎麼會一個台灣的導演去拍珍奧斯汀。但是他們說服了我,我去見了艾瑪湯普森,她也同意,就拍了。對我來講是抱著信念孤注一擲,我要下一個決心。我沒有去說服他們什麼,是他們說服了我,說會保護我。可是拍了以後發現其實我很怕那個保護,就是被他們掌控的感覺,那就是要去爭取、說服,這壓力很大,我每天拍完片就不太敢跟他們講話,拍到一半我胃都壞了,三個禮拜沒辦法好好吃東西,整個人太緊繃了。尼采說的:「What doesn’t kill me makes me stronger」(那些殺不死我的,會讓我更強大),所以就鍛鍊吧,不合理的要求就是鍛鍊。我很感謝過了這一關,尤其是這場戲我記得很清楚,這是在我電影生涯裡面記憶非常深刻的。開拍之後的前半天最痛苦,熬過去之後就覺得又有很多東西被我看清楚了,原來是迷迷糊糊的,後來視野突然就不一樣了。
我覺得拍片不光是藝術,它也是技術,不管是「藝」還是「術」,英文的Art是從希臘字Arte來的,它都是一個「技術」,「術」才可以講。有些腦袋裡面的想像或夢境,本來就是沒有譜的,可以講、可以溝通的東西就是「術」,「術」很重要,手抓到什麼東西,要怎麼去做才能呈現抽象的東西,才能讓看的人能夠有一些體會,啟發他們的想像,這跟你的想像又不太一樣,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手上的工夫。尤其電影是要合作的,要有很大的經費,我一直覺得基本功對我的幫助很大,當然不能完全相信基本功,如果這樣拍出來的話,就是很匠氣的東西,手上有基本功就是當你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,還可以繼續往前走,不會卡住。我那時候也是有一些基本功,因為他們看到我過去三部片,覺得我講話雖然笨笨的,但是電影還蠻好看的。然後不管怎麼樣,前兩天出來的毛片是漂亮的,這樣他們就會慢慢給時間,不會一下就把我炒魷魚。演員大概也知道我的狀況,交手一下就曉得,常常演員懂的比導演多,因為他們經歷過很多片子,導演都一頭栽在自己的世界裡,尤其是年輕導演,我那時候也還算年輕,演員們都會有感覺的,當他感覺可以把自己的形象交到你手上的時候,就會比較好過,就可以照自己的理想去做了。
Q:請問導演Coverage的拍法是每一條都會拍嗎?還是抓分鏡的重點?
李安:Coverage是比較屬於美國拍法,它屬於工業型的,讓大家要合作,拍的時候有個保險。花這麼多錢拍,如果你沒有cover的話,萬一掉了什麼東西要再去補拍、重拍就很貴。小片、藝術片比較沒有這個問題,導演拍一拍、想一想、看一看再回去拍,錢不多就沒有關係。如果演員很貴、場景比較大,用Coverage就很正常,所以是比較美國人的拍法。因爲舞台劇是從一個觀點看,電影跟舞台劇不一樣,可以鑽到兩個人物裡面去觀察,去描述他們之間的關係,有一個point of view(視角),視角可以變換,這是電影的強項,為什麼不用呢?我之前拍的幾部片都是很簡單的,兩、三個角色,像《飲食男女》一桌人,那我就分成四塊,兩個size,也都是蠻死的。像《理性與感性》這樣鏡頭有運動,人有高低,有明星,要拍得比較講究、不能出錯的時候,那Coverage就需要一點訓練,這算是基本功。
我覺得Coverage的好處是不會一下把戲說死,你可以關照到每一個角色,以做戲劇而言我覺得Coverage比單一視角拍攝好,單一視角用在你想調劑一下或是有特別重點的時候,導演的觀點怎麼去看它。單一視角是比較第三人稱,你進去一有主觀鏡頭就是Coverage。我這場戲跳出來是因為四個角色都有戲,除了凱特溫絲蕾的動機只有一個,其他人都有兩、三層。像艾瑪湯普森偷偷喜歡休葛蘭,不敢講藏在心裡,正室又是那個小三,她心裡很複雜,還有妹妹突然昨天晚上又發生了傷心事,所以她有四、五層的東西在那邊轉,她的視角非常多,每個視角都要cover的話,我可能要一個禮拜才拍得完,要多四倍的鏡頭數量,所以你就需要把它綜合一下,看怎樣可以在一、兩天把基本上需要的東西都講到,重點部分再切進去拍。還有不能拍得很死板,有時候攝影機要運動,保持它的流暢度,也要把它定出來。要想好一天裡面有多少鏡頭可以去拍,優先順序要定出來,副導才可以幫你算時間,才能去做前製準備。
重要性的次序要讓副導、工作人員知道,譬如有些鏡頭帶到就可以,有些要拍到漂亮,哪個鏡頭是重點,要多花一點時間,或者燈要怎麼打,艾瑪湯普森三十五歲演十九歲要進行很大的工程,要加什麼濾鏡等等,一大堆囉哩囉嗦的事情要處理。女明星頭髮沒弄好,你就不要混了,她們很在意,化妝也很重要,另外體態、服裝怎麼調整,這麼多事情都要cover到。你不把女主角弄到漂亮,她心情就不好,再加上休葛蘭也要漂亮,那個時代男人要戴假髮,但是像老頭子就不行,還有他的衣服看起來很矬,雖然那個時代的風格就是這樣,可是你就是要去調整。如果演員覺得你不在乎他,這就很要命,他心不給你很多東西就講不通,所以要伺候得當,每個人的心理都要在你的盤算裡面。讓大家在心情很好、很願意付出的狀態,把他自己釋放出來,同時鏡頭又要抓到,要跟片廠交代,然後你自己要的特別的東西也能捕捉下來。
從什麼角度去拍演員很重要,會給觀眾不同的感覺,尤其明星有很多細節要注意,你要了然於心,把他們弄得舒舒服服,當他們把心交到你手上的時候,事情就比較好辦了,讓他們的能量能夠釋放。如果你搞得他們很不舒服彆彆扭扭,戲就很難好。但也有時候你就是要那種彆扭的感覺,譬如像休葛蘭進來的第一個鏡頭,我就要去搞他,要是他太帥氣就不動人,所以我要去分散他的注意力。我記得是第七個take吧,我故意用中文的文法去講英文,讓他聽不懂,不過我現在英文講這樣也不能裝了(笑)。那時候我想說,整部片子只要有三個鏡頭,抓到他不曉得在演什麼就成功了,這是其中一個。我第一次拍明星不知道這些事情,把他當一般演員用,自己也是功力不到。
電影就是有一些東西你必須要服氣的,我到現在還在挑戰電影,我就是不服這口氣。電影本身有一種魅力,它跟觀眾有一個契約,不曉得是電影的本質就是這樣子呢?還是說我們在文化上面被訓練、被洗腦,電影就是有一個「電影就是這個樣子」的東西,有時候也由不得你,但我還是會繼續挑戰。我現在用更高規格去挑戰,給自己找麻煩,我會想說為什麼武打片不能這樣拍,有時候結果就是不行。武術指導會跟你說我們試了四十年,以前也跟你想的一樣,為什麼行不通會有一個道理。但是做為一個導演和自我存在的價值,你還是要挑戰,不服那口氣,不然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就會被刺激。該怎麼樣就怎麼樣的話,電影也不會有活力,新的人會想要試新的東西,觀眾會想看新的東西,但我覺得舊的東西還是很重要,它存在還是有它的道理。像為什麼休葛蘭是最貴的喜劇演員?你知道也好,不知道也好,反正你就是要把它當作一回事。因為他的角色在前面出現過,過了大概八十分鐘這場戲才又出現,其他演員可能就做不到,像他這樣一出場其他女主角心都碎了。休葛蘭就是長得這麼讓人疼愛,他可以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情,你不服氣也沒有辦法,這就是他片酬這麼高的原因。有他可能是一種負擔,但沒有他電影好像也很難成立。我是一半服氣、一半不服氣,做到後來都是不得不服氣,因為電影就是比你大啊,所以你必須要謙卑。
Q:請問導演,這場戲每位演員都有一個坐下、起來的節奏,是導演在拍攝之前就有這種想法,還是現場想到的?
李安:我事前有想過,可是他們一進來就打斷了,想了一個禮拜的東西就白想了,不過想那些東西也有幫助。他們做的表演有些可能有道理,你就必須要屈服,不能因為他打亂你,或是像休葛蘭這樣的大牌明星,你就不去想,這樣你會被他帶著走,就變成電影拍你,不是你拍電影了。我覺得最好是你都想過,因為想過以後,你會知道自己的原則是什麼,超出這個原則的時候,你可以跟他辯論,你有更大的理由說不能這樣做。你如果完全都不準備,邊走邊看的話也可以,有的導演會這樣做,讓演員自己演,像工作坊這樣,你再去採集再去想,幾乎是群體創作。我是不會這樣做,我會先想了之後再跟他們說,我把我的意圖告訴他們,如果他們有好的東西,我也會採納。
演員可以顧好自己就好,不用像導演一樣要有全知的觀點,但他最後要服從我,因為電影最後是我完成的。他專心想自己的東西就會想得比我多,這也是好處。做著做著當場就會發現排練的時候做不到的東西,現場的氛圍就是不一樣,會有一點火花,不要因為堅持己見就拒絕,這不太好。只有最好的演員跟導演才會反應,演員會說「Acting is react」,就是反應,好的演員碰到不同事件,他會有所反應,他是一個活人,導演也是一樣的。導演要讓人家心服口服,說服他們你的想法比較好,那演員有更好的想法也能夠放到電影裡面,彼此互相調適。我覺得沒有辦法完全做到心中想像的樣子,都是在現實和夢想之間磨合的時候產生一些東西,我們要尊重這個東西。做準備是應該的,要準備才有本錢即興。像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,準備了這麼龐大的東西,後來我還是要調整,因為有做不通或有更好東西,若不是在現場看到,你不會曉得,這個你就要調整。如果前面沒有做這麼多準備工作,就不會這麼靈光去調整,可能也有人天生就是這麼靈光吧,但我不是,我需要準備充足之後,知道自己要做什麼,保持開放的心態再去做調適、去做摸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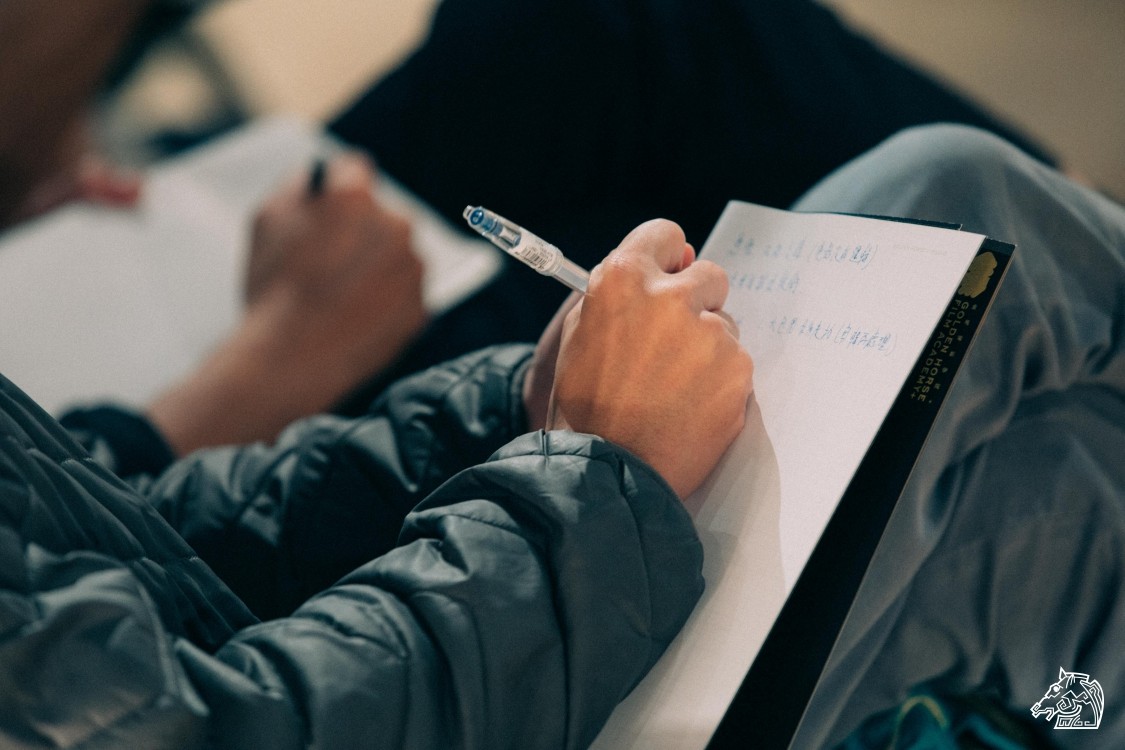
《色,戒》Lust, Caution
下一個片段就是比第一段要再高一級,我給自己非常大挑戰的一場戲,就是《色,戒》的麻將戲。我記得我們當學生的時候,老師教到《驛馬車》說最難的就是吃飯戲,有十二個人在一張長桌吃飯,他的連戲怎麼cover。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這麼方便,只能在課堂上放影片,看完老師就把劇本給你,你自己做一個分鏡表,他再給評語,之後再放那個片段,就會發現原來約翰福特的拍法可能比我想像中的簡單。或者是希區考克的《蝴蝶夢》,裡面的法庭戲有各個不同的角度,我們也是做這樣的練習。
《色,戒》這段影片是我拍過的Coverage裡面最難的,我要用方城之戰來表達一個很肅殺的氣氛,我要講的其實是戰爭片,可是我用幾個太太打麻將,用扭曲的人性來表現戰爭,它是帷幕裡面的事情,所以我就用方城之戰來開場。開場的時候一定要先定調,要讓觀眾知道主題、調性是什麼,像我就想要肅殺的氣氛,因為也有諜報片的成分,所以有疑神疑鬼的感覺,每個人藏著一些心事,關起門來的一種氛圍。扭曲的人性,有色、有戒,戒指、戒心之類的,這些元素一開場就要點題給觀眾。我就想到用麻將戲,麻將是方城之戰,它有好多個層次,首先是麻將的輸贏,還有這幾個太太的身分地位;在物資困難的時候,她們怎麼囤積貨物;這四個女人可能都跟易先生睡覺,也是我們講的「色」。她們要漂亮,誰知道什麼祕密、誰給誰暗示、誰話中帶刺、給誰什麼牌,這些東西其實是非常複雜的,七、八層東西在裡面攪和,怎麼去捕捉其實難度非常高。
我還蠻幸運,碰到一位李嘉茜大姐,她以前是李翰祥導演的助理,對打牌的文化非常熟,她是電視演員金滔的太太,金滔討了八個老婆,每天打麻將,牌經裡面都有階級關係,每天打牌勾心鬥角。李嘉茜就把這套牌排出來,老太太花了大概一個半月,排完之後她說「我這輩子的愛恨情仇都在裡面了。」這副牌我們把它記下來,每個take都是從頭拍起,打到什麼地方、該怎麼動作都要規定。拍到後來有一位大陸的女演員說:「導演我們全家都要感謝你,我再也不想打麻將了。」這場戲我們拍了兩個禮拜,一個禮拜拍六天,一天拍十六個鐘頭,雙機拍攝。每一個人有什麼心事都有不同的角度,所以雙機、打燈、演員表演怎麼弄,計劃了很久。我出了一本手冊叫「麻將天書」,裡面大概有七、八層的意思,每個人通通有規定,每一張牌出手,眼神怎麼樣,心裡在想什麼,眼神怎麼看、怎麼觀察,都要做很詳盡的規劃。她們還有抽菸、吐菸、吃餛飩,通通要記熟,其實就是連戲,所以整個很麻煩,比吃飯還難一百倍。拍了兩個禮拜,場記很頭痛,後來我們掉了一卷要重拍,他一想到要重拍,馬上頭又開始痛,要休息半天才能繼續。
這場戲我自己是非常得意,裡面有非常複雜的換焦,那時候香港最好的攝影師做二機攝影,都是頂尖的人,調焦距的都是拍過大片的大攝影師,都是武俠片拍到精的攝影組,拍得非常精準。我們主要的麻將牌是跟人家借來的傳家之寶象牙古董牌,跟塑膠麻將的聲音不一樣,湯唯用這副古董牌,戲就對了,不能用另外一副麻將來拍。其實拍這場戲覺得很有意思,但拍了十六個鐘頭眼睛都紅了,非常麻煩的一場戲,我們來看看。(播放《色,戒》開場片段)
Q:請問這場戲這麼複雜,那聲音是怎麼處理的?
李安:就是好的聲音剪接、對白剪接會幫你處理,處理不來就重錄,就跟動作片一樣。像這麼難拍的電影,要看什麼東西重要,如果對白很重要,那你就對著演員錄;如果牌的本身是戲,對白不是很重要的話,我就不會著重在聲音上面,現場能夠處理就處理,不能處理就重新錄。這場戲我可能還是以視覺為重,就跟動作戲一樣。
Q:所以最後並沒有用到兩副牌一起拍嗎?
李安:四副吧,因為湯唯的關係拍得慢,比較重要的戲、拍到她的臉時就用那副古董牌,搖過去的鏡頭其實看不太到牌,但是她還是堅持要用古董牌。有時候production(現場拍攝畫面)很吃重的時候,你可能就會要演員盡量配合,但是像這種戲女主角一出場,觀眾的心就是要被她勾著走,她是怎麼擠到太太們的生活圈裡面,都是很細微的東西。你碰到這種演員,如果聲音對,她的戲就很好,她才第一部戲也算天才演員,拍這麼複雜的戲就是她最大,雖然是新演員,可是她最重要。譬如說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就是水最重要,所有東西都是為水服務,演員就不要囉唆。一般演員都會知道,像我跟威爾史密斯拍《雙子殺手》也一樣,他會知道需要他表現的時候再發揮。湯唯可能第一次拍戲不知道,可是她有資質,雖然她是新人,看起來好像我在捧她,其實不是,我們也在新人身上抓到東西、找靈感,所以是很公平的。你要會取捨,有時候很細微的東西,你花很多心力去做是值得的,因為它是電影,它是想像的世界。
Q:這場麻將戲是分成很多段來拍嗎?
李安:這個就是很難啦,因為麻將順手,但燈光、演員不一定順手,這都要算在裡面。盡量以燈光來算,燈光是最花時間的,如果有大牌演員,就以他的精神狀況來算。譬如說今天楊紫瓊要哭,這是大事,那就以楊紫瓊的哭戲為主去安排時間,大家配合,每天都有不一樣的需求。《色,戒》這場戲演員都還蠻配合的,我就大概以燈光來算,不過有時候也是看現場拍攝怎樣比較順,攝影dolly有時候要先架起來,我才知道後面戲要怎麼配合,通常先拍大的鏡頭,小的鏡頭就比較容易了,如此一來怎麼連戲大家就比較有概念,演員演練熟了之後再拍近景,大家就比較好搭配。
我記得這場戲大概分四、五段,你也不能讓她們從頭到尾打牌,這場戲這麼複雜,大概以攝影機運動為主,大的鏡頭定好之後,看缺少什麼再鑽進去拍。我們是雙機拍攝,如果單機可能要拍更久,雙機要看角度的搭配,攝影組、場記、副導幫忙規劃,一天大概有哪些大的戲,拍完之後我們再來鑽細節、換焦。還有就是連戲的問題,她們的手要打牌、抽菸、吃餛飩,有時還要秀鑽戒,這些都要算進去,我一個人沒辦法,需要其他人幫忙,但是導演要知道大致的規劃。
Q:這種類似偷窺的攝影風格有跟攝影師討論嗎?
李安:對,有跟他們商量。因為我們的片型是黑色電影(Film Noir),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,就是黑色電影的精神,這個四、五○年代已經被拍到極致了,後來就有這種方法,也是做這種感覺。我跟攝影師商量說用顏色來區隔,還有一個大家都用爛的,就是用焦距跟角度,大家都在用,但我們是用顏色,什麼是明的、什麼是暗的,去想黑色電影還有什麼可能性。有些黑色電影的基本功,像陰影不用說當然是重點,焦距也是蠻大的重點,定焦在哪裡、怎麼去轉換,製造祕密感、情報感。
其實我拍這個片型碰到最大的問題不是攝影,是編劇。因為中文裡面沒有這個東西,黑色電影很重要的是對白,有一個特殊耍嘴皮子的風格,從比利懷德(Billy Wilder)的《雙重保險》(Double Indemnity, 1944)就用到精了,中文就沒有這個文化,這讓我很頭大。我們有一位編劇幫手詹姆斯夏慕斯(James Schamus)用英文去寫,那時候我已經比較知道怎麼用英文去表達,在《臥虎藏龍》的時候不是很清楚,《飲食男女》也是一直在想對白怎麼轉換處理,不只是翻譯而已。拍到《色,戒》的時候我就比較清楚了,我們要把它的精神拿過來重寫,所以我覺得拍黑色電影最大的困難就是台詞,把它的精神融入華語電影,而不是洋腔洋調的電影。
Q:您會特別去做什麼事情讓演員保持新鮮感嗎?
李安:最好是演員能夠自己調適,像新演員就有這個問題,一上來就掏心掏肺,才剛開始就把力氣用光了。資深演員就都知道不要這樣做,一般資深演員排練再多可能也是白排,他根本就不拿出來好東西,攝影機開始轉了之後再拿出來。那就是要提醒一下新演員,幫他分配,資深演員知道一天要怎麼過,新演員可能就太興奮,第一個鏡頭通常最花時間,一開始衝太猛後面就沒力了。還有一個重點,就是湯唯跟梁朝偉兩人的戲,我一定先拍湯唯,雖然她的天分很高,但是她的神是飄的,梁朝偉可以一直拍都還是很好,他自己會調整,所以我一定會先拍湯唯,再拍梁朝偉,反過來可能就不好了,所以你要幫她調適。那王力宏就是金牛座的,很帥、很飄逸,但其實他是苦工型的,第六條一定比第五條好,第七條一定比第六條好。
每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,你都要幫他們設想,像章子怡、凱特溫絲蕾還是新人的時候,我拍她們大概都十九歲而已,沒有太多經驗,導演就要幫她們。我拍過最奇怪的一個例子就是《與魔鬼共騎》,找了很紅的歌手珠兒(Jewel Kilcher)來演,我們拍了之後發現她演兩個小時就不行了,怎麼教都不行。然後她是眾星拱月,像陶比麥奎爾(Tobey Maguire)這些後來都成名的演員,都圍在她旁邊,因為他們的戲都在她後面,拍到後來她拍好,再拍他們的時候,他們都累了。過了兩天,還是我們的製片人經驗比較老到,他說可能因為兩個小時就是演唱會的時間(笑)。那我就趕快跟她說我們不是演唱會,會拍十幾個小時,講過之後她就好了。我覺得製片有時候會提醒,不過主要還是導演的掌控。
Q:您會在前期特別去瞭解這些演員嗎?
李安:其實無從瞭解起,就跟他們排戲,甚至要到開拍之後,自然就會注意到他們是怎麼樣的人,也就是觀察吧,拍久了就會有經驗。像我拍這部片就蠻有經驗了,《理性與感性》那時候就很折騰,要去幫助演員讓工作順利,成功機率就高一點,經驗還是有幫助。如果早幾年拍麻將這場戲,我可能拍不了,其他挑戰像床戲,精神折磨就很大,武打片也是,就是差不多覺得自己可以去挑戰它了。所以像這場麻將戲就很需要經驗,然後掌握工作團隊也很重要。
Q:像這場戲大概拍了兩個禮拜,當初您怎麼去說服劇組給這麼多時間?
李安:前期作業的時候都規劃好,以我的經驗,這種戲就是要拍很久,一般一個禮拜就很多了。我在練習的時候會去觀察排戲,想說要去捕捉什麼東西,再去分門別類計算需要多少時間。這個戲比較特別,通常製片說多少時間,我都會盡量做出來,不太耍個性的。這部片多拍了一個半月,這部分我自己出錢。你有資源、有優秀的演員、優秀的攝影師,就盡量讓他們拍,我覺得也是一種幸福感。有些電影是在做工,有些是任性,我今天挑出來的這些片段就是屬於任性的,我覺得應該堅持,有些需要妥協,但有些我一定要拍到。
在美國都把說故事擺在最前面,推動劇情最重要,要像追劇一樣要讓觀眾有好奇心往下追,他們覺得這是基本職責。我是很不信這一套,從來不會說喜歡一部電影是因為它的故事說得如何,但是會說喜歡某個moment或是一個sequence(段落),這是一個視覺性的純電影體驗,那是無法言傳的,故事只是把它們串起來。故事當然重要,但就不是純電影的東西。拍電影的時候,說故事、感動觀眾、加入社會議題都很重要,但我做為電影人,有些純電影的體驗才是我要拍電影的原因。我希望你們都有這種段落可以為它拼命,一定要做到過癮,把心裡的東西宣洩出來,那其實是蠻可貴的,但你也只能選擇,不太可能整部電影都這樣拍。
Q:像導演覺得這種重要的片段,您是會在前期就執行它,還是有別的計畫?
李安:不一定。這部電影有比較多任性的東西,抓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,很難用言語形容。這場麻將戲算任性、也算野心吧,學電影以來就知道這東西很難弄,所有最難弄的東西都加進去。另外也要比喻戰爭,沒有實際的戰爭場面,是用間接的影射,《色,戒》是色跟戒,《臥虎藏龍》是臥跟藏,我覺得這些東西很有意思。我在拍之前會盤算,我會跟工作人員、製片說:「你們不要給我打折扣,其他戲可能沒有關係,但是這場戲我一定要做到。」《理性與感性》我是去打工,別人給我劇本,我就是去導而已,但是凱特溫絲蕾的生病戲有珍奧斯丁原著的精髓,我就說你們不要煩我,這是我的電影,我就是要任性地拍,這也是很好看的一段。你會知道這部電影有某些段落或moment特別重要,或是你覺得非拍不可,那種追求是無以名狀的,其它起承轉合的東西只是供出需要的養分,當那個重要的段落來的時候,所有前後的東西都要去支持建構那個創作的可能性,這是比較藝術的東西,很過癮。
《斷背山》Brokeback Mountain
接下來我選了幾段學員們提出來的《斷背山》片段,還有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場戲。第一場我選的是《斷背山》的片頭,電影一開始的時候就要定調,還有就是我們講的Rules of the Game(遊戲規則),因為電影是一個封閉世界,不像人生什麼東西都有可能進來,你要歸納電影的主題跟調性,將劇情推演、人物行為在大概的範圍內定調,讓觀眾在心裡有個軌道可以進入。譬如剛才《色,戒》說的肅殺、爾虞我詐的氣氛,開場從一隻狗的眼睛轉到人的眼睛,警衛森嚴,浮華頹廢的上海,我就是這樣定調。配樂我就用了瑪琳黛德麗(Marlene Dietrich)的歌,第一代的性感女神,其實《色,戒》的小說,我看很明顯就用了三部電影,其中一部是她演的電影,是演女間諜愛上她的獵物,所以我就把主題曲放在這個地方,這首歌有一種很委靡頹廢的感覺,很像《酒店》(Cabaret)的那種感覺,我就把氣氛定調下來。
《斷背山》我要定調什麼呢?西部片其實是人造的東西,兩個人開槍對決,那完全是電影造出來的。我告訴大家我們要做一部比較真實的西部片,不是傳統西部片的西部片,而是呈現真實的西部精神。同時也要呼應傳統西部片講究的精神,它講究戲劇性,然後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,就是它們對空間的處理,這是我發覺到的。當時編劇很質疑我,他們覺得都市人不可能懂美國西部,更不要說台灣的都市人,可是我的內心是中文的傳統,這東西難不倒我的。他們覺得這不像《理性與感性》可以完全用講話來表達,是語文性的電影,他們覺得《斷背山》更難,但對我來講不會,因為在中文傳統裡面,我們對於空間、形象的處理本來就很強,我們也是很壓抑的,所以這個東西我還蠻有把握。
我就要把它定調出來,在偌大的自然環境裡面,人是非常渺小的,無奈壓抑,愈奔放愈壓抑的感覺,這是我的西部片要表達出來的東西。還有蒙大拿州、懷俄明州的天空感覺特別大,因為銀幕的大小不一,你不知道投放出來的感覺,所以要靠一些雲,不但是空間的運用,還有裡面的細節質感,雲跟風就變得很重要,這樣才會感受到它的大。另外除了空間的空間,還有時間的空間。他們常常沒事找事做,浪費時間虛耗生命,你看到每一句話中間有很長的沈默,這就是空間感。然後我們的音樂彈了一下,停個半天再彈第二聲,這也是空間感,我要提示觀眾這部電影是在處理時間跟空間。它原本是一個短篇小說,我們要把它變成一個史詩般的愛情片,那就要靠空間、時間的伸縮性。我們必須在第一場戲,還沒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就把它點出來,不管什麼電影,觀眾大概會給你十分鐘,過了之後他就要追他想追的東西,所以一開始還可以這樣做。
另外這種西部片裡面的人物就是牛仔,他們很注重pose(身體姿勢),話不多很害羞,他們是用body languege(身體語言),不是用言語去表達的文化。《理性與感性》是一堆人不停地在講話,這部片完全相反。西部片中人與人間的化學反應要靠身體語言去表達,所以就變成要有pose。開場的這場戲,兩個人什麼事情都還沒有發生,大眼瞪小眼,然後身體怎麼樣對應,這要靠排練。這一場是我選擇的重點排練戲,他們不認識,也不要講話,就在等,接著開始去感覺對方,然後我就看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東西,再記下來跟他們討論。所以這場戲其實是我排練的,劇本裡面沒有,劇本裡面只說他們兩個在等,然後老闆來了,對我來講,這是拍得很足的一場戲。因為我們跟演員在做即興表演,給他們一個動機、一個情境,兩個人悶在那邊看很久,看久了就有一些東西出來。那我們來看看這段。(播放《斷背山》開場片段)
Q:照後鏡的意象是怎麼抓到的?因為小說沒有這個畫面。
李安:小說就三十頁,沒有這些細節的東西,尤其他不講話的話,細節就非常重要。你想看人家,又不想被人家看到,照後鏡就非常重要與方便。照後鏡本身是不動的,有一個人在裡面搖動的時候,會有一個情愫在裡面,很好用。電影其實就是一種偷窺,法文叫Voyeur偷窺狂,你窺視到別人的生活有某種爽的感覺,這就是電影。對我來說,能去觀察別人就蠻重要的,不需要台詞去說我對你怎麼樣,你對我怎麼樣,這是一個private(私密性),只有你跟那個人知道,或另外一個角色不曉得,別人都不曉得,有這種好處在裡面,這就是種間接表達。鏡子是蠻好的一招,電影裡面常常會用到,鏡子的構圖很有意思,也有自我反射的作用,算是一個好用的工具。
Q:畫面中有火車經過,這是劇本就有的,還是現場決定的?
李安:勘景的時候有靈感,我覺得這樣拍一下蠻好的,因為它每過半個鐘頭就有一趟,而且這個火車好像在送長榮的貨櫃,出來有點煞風景。我們會先架好攝影機,然後去跟鐵路局商量,跟他們說我們大概要拍的狀況。尤其是像這種山景,不到現場勘景不會有那麼多靈感,很多靈感都是看到那個地方,產生很多的想像。這部片子的配樂家Gustavo Santaolalla後來得奧斯卡獎,他來面試的時候,我就放了兩段音樂給他聽,他很想拿到這個工作,過了一個禮拜他就做了五條歌、七首曲子,後來一成不變地放到電影裡面。那個音樂我就帶在身上,分給演員、工作人員聽,勘景的時候反覆聽就產生很多靈感。後來我發現他不會作曲,他沒有做過訓練,他就吉他那樣彈。我跟他講一大堆怎麼配弦樂,講了幾個月編不出來,我後來就跟負責管弦樂的人一個音符一個音符湊出來。搞了半天他不會作曲啊,把我頭髮都急白了,結果他連續兩年得奧斯卡,都是吉他彈一下就得奧斯卡。
Q:因為像這種情感片,兩人情感交流非常重要,後照鏡的鏡頭是不是導演一開始就讓他們兩人彼此會有connection?
李安:對,這部電影是個愛情故事,會動人是因為跟渴望、壓抑有關係,不是說只有私密感、性的表現,這是一種private的感覺,找不到語言來形容他的感情是什麼。因為在那個時代,他沒有同性戀語彙的瞭解跟表達能力,那希斯萊傑又是一個恐同的同性戀,所以他是一個充滿內在張力的角色。傑克葛倫霍就比較漂亮、比較開放,他是比較勇敢的角色,他可以去面對,因為他比較開放。原先小說不是愛情,就是很苦的小事情,我看過劇本後想說電影總是要去沾到一個類型,後來我決定把它當愛情片。我選擇當愛情片處理也是有關係,這個愛情片跟壓抑與渴望有關係,因為他話又不多,一定要用山水去做出那種說不上來悶悶的感情,聽了又很澎湃、一口氣又出不來的感覺,你就要去經營、掌控,他沒有辦法表達的沉默一開始就要定調。
下一場的要放的是一位同學提出來想看他們分離的一場戲,那個分離除了渴望之外,還有一個惆悵的感覺,惆悵就是比較難做的東西。他們花了二十年,一直想重返斷背山,斷背山是一個虛無的東西。他們在斷背山上的時候,不曉得這是什麼感情,兩個人打了一場架分手,分手也說不上來是什麼感覺,他們花了將近二十年去尋找,想要回到斷背山又回不去,他們也沒有在一起,所以最後傑克抱怨說:「All we have is Brokeback Mountain」(我們擁有的只有斷背山)。當初就是小說這句話讓我想拍這部電影,我們有的只是斷背山,什麼都沒有,只是一個存在主義、一個很虛無的東西,還有他的渴望。其實這個用電影具象去表達相當困難,它需要很多的texture(質地)、很多的空間、很多的壓抑,包括一些美感的東西,去追尋一個惆悵感、一個捉摸不到的東西、一種迷惑感、一種失去,這就是小說引起我想拍電影的主要原因。所以我捕捉的也是這個,失去一些東西,然後要抓回來。我的人生裡面有很多,但是不告訴你們是什麼東西,常常會有這種抓不到、悵然的感覺。
Q:跟傑克講戲的時候,你會很明白地告訴他,你需要這個感覺,還是只會跟他說做什麼動作?
李安:我覺得最好都不要告訴演員演什麼,尤其有些東西是沒有辦法演的。你這樣拍,他這樣演,加起來好像就有這麼一個感覺。你跟作曲的講,作曲就覺得都是他做出來的,跟導演講,導演就覺得都是他導出來的,演員也會覺得都是他演出來的,變成每個人都會過度表演。那電影是綜合的,每個人知道他該做的部分其實比較好,演員需要有個距離,不然他沒辦法演,你跟他講悵然,悵然沒辦法演,演的話就會很過頭。
我有時候會讓他去想其他事情,不要讓演員去想主旨的東西,抽象的情感是不能演的,演員沒有辦法重新創造一個情感,所以我們要做的是sense memory(感官記憶),用記憶裡感官的感覺,回想起那時候是怎麼樣,然後觀眾會幫你演。演員有動作,可以刺激觀眾去想,你再怎麼演,演不過觀眾的想像,所以演員的工作只是去刺激觀眾。做為導演盡量不去跟演員講感情的事情,也不跟演員講抽象主題的事情,我可能在排練的時候大致提一下,拍的時候我盡量不要講,就好像接下來要放的這場戲,你跟他講難過、追求不到,但這跟他有什麼關係?他只要去做他當下該做的事情,管好他走路,這個戲就出來了,我是這樣認為。
下面我想放一場他們要分離的戲。你的腦筋要清楚這是自己要捕捉的東西,你的鏡頭堆砌、分配,然後他有幾個對白。演員因為他的壓抑所以欲言又止,觀眾想替他講出來,做為演員他要想到,要去講沒有講出來的話去勾引觀眾,勾引觀眾的本質是他的工作。這個工作你就要跟他講清楚,可能因為個性害羞、因為上次跟人家打架,講這些很務實的理由讓他去演,他沒有這個意思,可是觀眾的腦海就聯想到他們兩個在一起,聯想到他們當時該講的話沒有講,以後就後悔了,後悔也沒有辦法。所以這是觀眾的事情,我不會跟他們講。
有位同學想看這場分離戲的最後一顆鏡頭,這是我電影生涯裡面大概前五個最得意的鏡頭之一吧,就這樣給我拍到。希斯去打牆壁,打到第三條就流血了,時間也到了。美國西部最重要的風很大,有枯枝的樹枝球被風吹滾過去,很有氣氛,然後雲彩也出來,前一顆鏡頭都到位,但覺得還不夠,不夠還能怎樣,光影再弄一下就再拍一個。演員手都出血了到底還要不要拍,太陽又要下山了,還有幾個鏡頭要拍,最後弄一弄就拍到了。還好有堅持一下,拍到之後製片也沒有話講,演員也補足了那個東西。勘景的時候就有那顆鏡頭在腦海裡面,所有的鋪排、鏡頭的堆砌、情感的欲言又止,一步一步怎麼樣堆砌到那個點讓它爆發,都事先計劃好的,不光是當天發生的。我們帶技術人員去第二次勘景的時候就已經規劃好了,講好幾點拍什麼、光怎麼樣,每個場景都在山區,距離住處大概都一個鐘頭,所以最好要一天拍好,這是需要計畫的。 (播放《斷背山》兩人分離暗巷片段)
說到那個後照鏡,如果是用Motif(母題)的話,我起碼會用三次,就是要呼應。不然突然一看好像是無意的一樣,如果是有意的,我通常會用三次,像這邊又出來一次,我會大概規劃一下。
Q:想請問為什麼會選擇在防火巷讓他乾嘔?
李安:勘景的時候看到,排戲的時候再確定。其實劇本很簡單,一般的拍法就是話講完之後就走了,但是他還是會要吐啊,吐就一定要找暗巷,不會在一個空空的地方吐。所以找景的時候就找這種,像觀景一樣可以看到外面的,這部電影裡面用了蠻多把人鎖在裡面,然後外面有風景的畫面。最後一顆鏡頭也是,窗子外面的景很開闊,但人就是鎖在裡面,這就是壓抑。這種鏡頭最怕的就是什麼都好,但後面的臨時演員演過頭,這就要管住,電影很奇怪,前面九十九個元素都好,後面只要有一樣不好,大家都會注意不好的東西,臨時演員常常會有這樣的問題。你前面做得再好,後面沒有管控到的話,整個畫面會被影響,需要非常的注意。
其實劇本很簡單,排戲的時候你告訴演員很多動機,他們會給你一些靈感,在拍攝的時候就要注意細節。那場戲只有幾句台詞,應該是要拍很快,但拍了老半天,可是我覺得值得。因為戲都在字裡行間,不是在字本身,聲音表情當然很重要,可是字裡行間暗示著他為什麼要講那些話。希斯是希望傑克不要走,但牛仔的個性是很ㄍㄧㄥ的,那種很硬漢的東西不適合講出來,真的要靠演員去演,演員要夠靈光,他們準備的條件要夠。這就是剛剛講的,勘景會給你很多靈感,我覺得像這種不是以台詞為主的時候,那個景就是人的內心風景,它要反映出人的心情,你要用圖畫說故事,所以找景的時候,你其實是在幫助他們的演出。但你幫他的時候可能他就會過頭,你就要去控制演員不要演到飽滿,因為我的鏡頭是飽滿的,演員只是其中一個要素,演出當下該做的事情就夠了。好的演員都知道這些東西的。
Q:在勘景之前就設定要找防火巷,還是你原本有其他的想像?
李安:我在找暗的地方,後面可以看風景的,先看風景我喜歡,再去附近巷子看有沒有窗戶可以進去的,通常都會有個目標。那個東西讓你刺激想像以後,就去想我在這邊可以做什麼事,有時候不是直接把人擺進去就好,需要透過前景、後景去襯托,那就去找這些元素。現在你們這一代拍攝沒有我那時候麻煩,像這個前景搞不好在片場就可以拍,把景片搭上去,當然演員就沒有現場感,但其實是可以更方便,時間更充裕。我們以前的拍法很笨拙,很多的不方便,但帶來很多創意,不過有時候不方便就是不方便,方便的話你可以多拍一些,或是有更大的自由度去拍到理想的狀況,讓演員更舒服可以表達。有時候運氣沒那麼好,雲沒有那麼漂亮,四點鐘陽光沒有那麼好進來,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,真的是這樣。
《臥虎藏龍》的武術指導袁和平常說:「電影是遺憾的藝術」,很多都是遺憾的,這個做不到、那個做不到,如果能夠切開來,用不同環境拍,你的創作自由可能是更大的。這是數位電影比較可能做到的,有時候我在想你們會用得越來越多,像我這代有些導演根本不喜歡勘景,覺得浪費時間,像我就很喜歡勘景,因為勘景讓我很快地去思考這部電影,很多想像力是從勘景來的,不見得是拍片。至於看到演員就是另外一種勘景了。等下要放的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就沒有辦法勘景,你不可能到海上,不可能有一艘船給你,就只能靠動畫勘景。
現在我都放比較set up(設計)的戲,等下我放一場比較有戲劇張力的戲。在美國我拍家庭戲特別喜歡拍感恩節,因為有點像我們的中秋節,但又不一樣,我就是跟感恩節過不去,我拍《冰風暴》跟《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》劇情都是在感恩節,然後還有三場戲,包含《斷背山》有兩場。我覺得感恩節是戲劇爆發非常好的點,大家表面上一團和氣,一家人一年見一次,什麼恩怨都會爆發,很多東西都準備爆發。我就從前面一場戲開始鋪排,大家一團和氣,連小孩子都很世故地看著父母跟繼父,最重要是女主角蜜雪兒威廉斯怨婦強顏歡笑的樣子,很好玩。
吵架的戲我最喜歡放在廚房,你剛剛問麻將戲錄音可能有問題,但最痛苦的事是洗碗的戲。我特別喜歡拍洗碗的時候,因為見面三分情,真心話不太會講出來,真心話在兩個地方最容易爆出來,一個就是在洗碗的時候,不用看著對方,手上又有事情做,這種時候最容易爆發;還有就是開車的時候,是懺悔的最好時刻,因為眼睛看前面,不用看對方的臉,所以很多內心的東西容易表達出來。我拍過很多次在洗碗槽的吵架戲,這場戲比較不一樣,就是兩個人面對不同方向。那時候我很喜歡用雙機拍,雙機可以取到不同的size跟角度,越側面就會越客觀,另外一個人就比較正面,一個是主觀、一個比較客觀、然後你再換一個角度,接著光就直接過來,一個正光、一個逆光也很好,戲劇效果都很好。這時候吵架爆發,不管是中景或是近景都很帶勁。所以從氣氛醞釀到吵架,到吵架以後情緒的發洩,就是這一段拍的內容。放給大家看看。(播放《斷背山》感恩節片段)
我覺得好像老天在幫我拍這部電影,電影之神對我蠻好的。我拍完上一部片很累,這場是在半睡眠的狀態拍的。我拍電影到現在三十年,就這部有時候早上不太想起床,剪接的時候也很累,毛片都沒看好幾次才初剪,所以電影不是努力就有用,有時候要靠天命。這場戲每個演員都好,包括小女孩都是臨時找來的,演得很好,那種世故看著雙親的感覺,非常準確,拍了一陣子你就有感覺。拍這部片之前其實我想退休,因為我父親剛過世,他沒有鼓勵我拍電影,我在四十九歲的時候帶我兒子回去台南跟他過年,我出國以後二十多年沒有在家過年,然後他就問我說你要不要教書,從我出國念戲劇開始,他就問我要不要教書。後來他跟我說你才四十九歲,如果退休會給小孩不好的示範,就再去拍一部電影吧。
兩個禮拜之後,他突然就過世了,我就趕快趕回來辦後事,其實我並沒有時間去感受悲傷,處理完追悼會我就直接跳到這部片做前期,我覺得我不能停下來,我爸爸第一次鼓勵我拍片,他還是引以為榮嘛,我就抱著這個心情,抓著我三年前還沒有拍的電影,它好像是在等我一樣,我就在半睡眠狀態這樣拍。週末製片還逼我去遊山玩水,當時在加拿大拍的,剛好在打冰上曲棍球冠軍賽,我去看了八場,正在拍攝期,人家看電視轉播我也跟著看,之前拍電影從來沒有這樣子,跟《色,戒》的時候完全相反,其他電影都是全神貫注,我覺得大概是天意要我繼續拍電影,就繼續做吧。在那個環境拍,演員都二十出頭,演到中年還演這麼好,其實也不是我教出來的,有時候就會碰到,我也有碰過從大到小每個人都讓我很頭痛的,這些都經歷過,也是一個奇妙的經驗。
我想再放一個片段,這是很stoic(壓抑隱忍)、很簡約的一場戲,情感非常凝聚,很稀薄的。我想到一位丹麥畫家威廉哈莫修依(Vilhelm Hammershøi)的氣氛,我就拿給藝術指導看,他就直接畫那個景,我去拍的當天感覺就特別好,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場戲,因為他在捕捉一種失落的感覺,還有他在表演傑克死掉後大家對他的想念。我覺得這很抽象,但他們做出來了,那天我到了開始走位以後,決定用拍《綠巨人浩克》的拍法,幾乎是亂拍。鏡頭放在對戲演員的兩邊,然後拍到幾條滿意的就一直換鏡頭,演員不知道往哪裡演,然後找一些特殊理由去拍一些角度很怪異的東西,然後我還跳線(cross the line),但是剪得都很順也沒有問題。然後希斯什麼都沒做就讓你很揪心,這部片之前他主演的戲沒有紅起來,我在想是不是他演配角時搶戲,而演主角卻紅不起來。後來我拍到有一場他跟前任女友在巴士站吃蘋果派,一句話都沒講,那個女演員演到又是流眼淚、又是怎麼樣,演得非常好,但都是她在演,希斯就在那邊吃蘋果派。我們放毛片的時候,所有人都在喊「Leave the man alone」,我就知道這個對手女演員怎麼演都是白演,希斯什麼都不必做,但是戲都在他身上,這時候我就知道他是一個天生主角。
演員真的有這種什麼都不必做,可是你心裡都往他那邊跑,別人都在陪襯他,沒有什麼天理,所以老天很不公平,希斯就是這樣的演員,這場戲也是,這兩位演父母的演員好得不得了,都是舞台演員不是電影咖,希斯什麼都沒有做,光坐在那邊就很揪心。早上去還沒有拍的時候,我一看天色就知道今天是很好的一天,一直到晚上拍完收工,全天都很順利,天也很美,演員也很好,要拍的東西很順,拍完以後看到雲彩不錯,又多拍了一個Cut Away鏡頭。我剛剛那些戲講Coverage,但Cut Away很重要,可以幫忙剪接,需要一個什麼都沒有關係的鏡頭,不過像這場戲就不需要,它的Coverage跟一般電影是不一樣,角度很奇怪,鏡頭也一直跳,但就是剪得通。所以我覺得平常說電影要怎麼拍,好像有道理,也沒有道理,看久了也會有種膩味,跳來跳去也還蠻好的。(播放《斷背山》希斯拜訪傑克父母片段)
你可以看到即使一團祥和,也有演員的張力在裡面。希斯殺青之後就跑去演一部喜劇,一收工第二天就上飛機,宣傳的時候還說他需要輕鬆一下,所以去演這部喜劇。拍《斷背山》的兩個月裡面就是咬牙撐過去,很認真的一個演員。
Q:演員會有一些小動作,例如說演父親的演員講話講到一半,對著杯子吐一口菸草,或是希斯面對第一次分離走到暗巷吐、搥牆壁哭,我很好奇把這些情緒變成具體動作,是在劇本階段就有的嗎?
李安:吐在劇本跟小說中都有,這是壓抑的人情緒爆發出來,原本就有,但是堆砌到那個情緒,劇本跟小說是比較沒有。本來就是兩個人分開了,一個人開走,一個到旁邊就吐出來,但沒有花這麼長的時間去醞釀這個情感。這是我們拍電影的事情,不是編劇的事情,編劇提供出來,然後你要看怎麼去發揮。有時候演員會有想法,像父親吐菸草的戲,他只來演一天戲沒什麼說話的分量,他會請教我說我這樣吐可不可以,說哪句話才可以吐,這都是比較細節的。
像這種通常都不太排戲,那時候已經開拍了,如果要排戲,週末就要工作不能休息。除非他們來了我們又需要勘景,檢查景的時候讓演員走走位、講講感覺,這些都要演員跟工作人員特別同意才有,不然就是當天排。像這麼大的重頭戲,我可能在開拍前會讓他們先排演一下再回去,可能一天、半天,好的演員會給你很多建議。但有時候也沒有辦法,因為事實上沒有辦法排戲,那你就叫他們照著演,這樣也有。我喜歡拍一拍聽他們意見,很多時候靈感是在拍的時候,他怎麼演你就有靈感。可以從監視器看到電影感啊,人的神情啊、角度啊。像演父親的演員,他有個角度,燈打了眼睛有點透,看起來有點賤的樣子,這都是到現場,燈放那邊之後才發現。所以現場很重要,最重要的就是拍片當天,其他都在醞釀準備,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想法都是在現場反應的靈感。


《臥虎藏龍》 Crouching Tiger, Hidden Dragon
接下來我放兩場比較不是Coverage的拍法,它們都蠻複雜的。《臥虎藏龍》竹林戲是我的重點戲之一,因為我知道青綠色在道家是最神祕的東西,片中有玄牝劍法、青冥劍,從無生有、從陰到陽,本質與現象的對比。陰陽又有男女的關係,所以綠色代表「生我之門,死我之戶」,我們的大俠就是死也要往裡面衝,生也是從這邊來,很多的意象在裡面。綠色又是電影中非常難處理的顏色,綠色跟紅色都很難處理,但我的經驗裡面綠色大概是最難處理的。這場戲就是綠色有兩個白點(人),基本上綠、白、黑三個顏色,所以我腦袋裡很早就有構想。大隊人馬拉到江南去看竹林,不光是竹林還要大吊車吊鋼絲上去,這都是以前沒做過的事情。你要到農場看景,景你要喜歡,還要搭前景,然後我去了之後才知道竹子砍下來十分鐘葉子就縮了,我以為跟花一樣可以弄個半天、一天,所以難度非常高。
再來軟的東西都難做,武術指導就不喜歡做,輕飄飄只要軟的他就不想搞,像三節棍、鞭子都不喜歡搞,更別說這種吊鋼索的東西,沒有著力點,困難度很大,地方又遠。可是這是我堅持的東西,雖然它沒有推展劇情,就是完全停下來做情緒的宣洩,非常的任性,很折騰人,又有危險性。對我來講綠色的意象非常重要,這場竹林戲因為輕柔,也是最性感的。《臥虎藏龍》龍跟虎就是道家講的情慾,所以他們講降龍伏虎,修煉那麼多功夫最難克服的就是情慾問題,人的情感是最難克服的。人生存的自然慾望,一個是吃東西,一個是性,這場戲其實就有性的感覺,但是你要把它藏起來就要用間接的意象去表達。這對我來講很重要,不是故事而是意象的表達,很難處理。
我有四個層次必須把它分清楚,第一個在意識上面,故事的本身是一個父權的象徵,還有女孩子的叛逆,還有收徒這件事,沒有拜師不能拿青冥劍、不能學玄牝劍法,你會走歪,這是道統的觀念,但這女人就是不甩他,道統是你們男人的事情,我們女人不管這個東西。《色,戒》也是在講這個,女權跟他們的對抗,這是意識上的,然後潛意識裡其實是在拍性,你要性感,但又是壓抑的東西。他跟俞秀蓮是明白的愛情故事,跟玉嬌龍是一個莫名其妙的追尋,所謂「藏龍」,很奇怪的情愫,所以你是在拍性,但又不能用性來拍,所以竹林跟綠色就是陰陽潛意識的層次。
另外還有下意識的層次,就是他們兩個有陰陽對比,不光是男跟女,一個是溫厚明白的大俠,一個是恰北北的女孩很衝,外陽內陰、外陰內陽。李慕白是外表很陽剛父權,內心其實是哈姆雷特、非常優柔寡斷的儒俠,他內在是非常陰柔、很折騰女人的,把俞秀蓮搞死了,一堆毛病搞不定;玉嬌龍外表陰柔,內心其實非常剛烈,所以有陰陽、個性的對比。拍那場戲的時候,人的面向要特別注意,周潤發很溫厚圓潤與跟成熟,章子怡就比較厲害、硬的,他們有個對比,這個是下意識的對比。還有一種是無意識的,這個人為什麼要這樣做,干他什麼事情,女的為什麼要跑,人的潛能裡面有個奇怪的東西讓我們必須去追尋,最神祕的力量,你都要放在這裡面。場景這麼難控制,有幾個大的鏡頭跟意象要先把它定下來,然後你要跟武術指導團隊溝通。輕的東西最難弄,每個演員下面都三十幾個人在拉,做出輕飄飄的感覺,那時候沒什麼電腦,就是真的人吊起來去弄。
這場戲拍了兩個禮拜,補了些近景,拍這種戲其實是要Assembly,鏡頭拍到一個你就要偷笑了,你要擔心人的安危,所以它其實是一個線性思考。在做線性思考時要用Coverage拍,不cover的話沒有辦法表現多層次,多層次一定是一種組合,你要嘗試讓它們激盪出來。如果你是一個單線的事情或單一視角的話,它會比較線性,當然你可以說裡面豐富的層次很多,但在一般觀影者的直觀上你並沒有提供他一些可能性,所以一定要用Assembly的方法去做Coverage的觀念。那你在cover的時候,幾個大鏡頭、幾個重點戲你一定要抓住,然後其他就讓他們發揮。鋼絲吊得如何就看個人努力,好多人都拉到吐,演員也很受罪,也有危險,怕掉到山谷裡面。當時香港的技術獨步全球,發展出非常聰明的道具組,怎樣欺騙觀眾的眼睛,讓你以為看到什麼東西,但其實不是,我學到很多東西。他們也很不習慣拍這種東西,所以就是彼此合作。拍出來的成果我覺得有拍到我想要的,感覺蠻性感的,綠色處理得也還可以,要謝謝武術組。(播放《臥虎藏龍》竹林片段)
拍這種我就覺得說,電影其實是在處理一個夢境,有些可以做到夢境的樣子,我覺得一定要把握住,要有很多準備工作,事實上拍也拍不到想要的一半,要拍到心裡想的或夢境那樣就很難,但很值得去爭取。
Q:我非常喜歡這場戲,因為李慕白、玉嬌龍的火花太好、性張力太好,相比之下李慕白與俞秀蓮的愛感覺不是同一個等級,想知道導演怎麼去處理兩段關係的平衡?
李安:很不公平,對楊紫瓊很不公平,面對十九歲的新演員,大家要講國語,她國語又不好,她的壓力很大,但是戲很多都讓玉嬌龍給搶走了,電影的設計中有人要扛戲、有人要搶戲,各司其職,玉嬌龍的角色「藏龍」跟這個無名的追求有關,所以觀眾很自然就會被吸引,那我也沒辦法,拍電影常常就是這樣不公平,當無理的東西被做出來,觀眾很自然地就會被吸引,當然章子怡本身非常出色。我非常瞭解李慕白跟俞秀蓮的性格,因為我平常就是這樣子,玉嬌龍就是藏的龍,人的情慾是無意識的,還有天生本性上就有些奇奇怪怪的東西,不曉得為什麼追求,我就往我的幻想、我最不瞭解的樣子去拍玉嬌龍的部分。如果是我瞭解的,我就不拍,如果她的行為是很合理,我就不要她這樣演,但是你也可能把她拍砸。原來也不是選擇章子怡來演,她就有這個命,而且剛拍時我還很擔心,第一個月很傷腦筋,後來山不轉路轉,看到她有種性感的潛質,整部戲就變了。
我原先想的竹林戲也不是這樣,拍章子怡一個月後開始愈來愈清晰,就堅定要拍竹林。本來武術指導非常不想去,武術指導說導演你是想要拍戲、拍打、還是拍場景,你選一樣啊,你又跑新疆、北京、山西、又去江南,專門去找一個竹林,竹林還不完全在浙江,有些在安徽黃山裡面,有水的地方非常麻煩,他們相信力從地起,在那邊每天吊鋼絲不著地,結果也很難預估,他們真的很不想拍這些,所有不想拍的都在裡面。但這對我很重要,拍出來的時候大家都很高興,一個虛無飄渺難以捉摸的東西。也是因為我拍章子怡,很多都是拍了她一個月以後有靈感,這個是比較後面,在拍了兩個多月後才去江南拍的。
Q:請教導演,中間有一場大漠塞外的戲,原本是劇本就這樣寫,還是後來剪接的時候放進來的?
李安:大漠戲是小說與劇本都有,但其實《臥虎藏龍》的劇本原來只有一點點,沒有寫什麼東西,第一版劇本是我把小說的故事告訴美國製片詹姆斯,他寫出來短短的一本,然後去找錢,他在劇本的第一頁就說,相信李安會拍最好看的打戲,裡面就一堆武打戲,就這樣什麼都沒有。後來我在前製勘景的路上,才去找王蕙玲寫劇本,寫了之後詹姆斯看了又覺得這樣不行,片子是要賣全世界的,很多東西他根本不知道在寫什麼,我就只好很辛苦地改。
開拍前一個月前就要把劇本給楊紫瓊、周潤發,他們習慣講廣東話,需要很多時間練習,還講不太準,但也沒有辦法。有時候甚至劇本是前兩天才寫出來,我為這些台詞傷透了腦筋,這場竹林戲除了「當日古寺留一步給你,是要見你的本心」、「你們這些老江湖,怎麼見得到本心?」這兩句台詞,其他隨口的台詞都是臨場寫的。這部電影很多拼湊出來的,我拍到一半想說完蛋了,不曉得在搞什麼東西,一直到拍完了也說不上來,剪接的時候也是。最痛苦的是周潤發跟楊紫瓊的廣東國語,做後期的時候花最多的時間是給他們配音,北京的錄音師說「還是楊紫瓊自己講比較有感覺」。我說算了不要配了,配這些大牌演員的口音也沒有用,就這樣上片了,所以電影有命,不是你能要求的,這部電影中每個演員都讓我頭痛,不讓我頭痛的演員就是廣東口音讓我頭痛,戲中很多都是武打,這些演員平常都是演戲的,突然做這麼多武打動作,真的很挑戰。電影說不上來,有衝動就盡量做吧,很多劇本都不是劇本裡的,都是後來加的,拍一拍有感覺就加,有我寫的,大多是王蕙玲寫的,也有詹姆士的要求,他以西方人的角度看這段覺得薄弱,要我去補足的。
Q:我很喜歡這場竹林戲傳達出的訊息,景與兩個人之間的互動、調情並且與自然混合在一起,我想要知道導演在拍這場戲的時候,因為你不可能去竹林上面拍,你要怎麼去排戲,如果我們的戲是有互動的,我們要怎麼去排這場戲?
李安:拍動作戲,你要記住你是在玩人家的命,所以負擔很大,動作或打鬥很複雜的戲,演戲很容易受傷,這是我們職業道德,稍微有危險性的戲,千萬不要跟演員講戲,尤其是武行,他很有可能會受傷,這個我們要負責任。如果近景、拍表情、有戲的時候,我就會搭一個平台,讓他們站在平台上演,他站在平台上,你就可以講戲。你一定要特別規劃,讓演員可以安全安心的演戲。謝謝你的提問,這個對拍動作片很重要,有危險性、有動作的戲,不要跟演員講戲,演員可能會受傷。
Q:導演我想請教,這個技術層面看起來很複雜,現在如果重新做這樣的劇情,你覺得後製的拍攝與實際上去拍,調度上會有差別嗎?
李安:會,現在要我拍我也不會這樣拍,當時的拍法是去玩人家的命,我拍的時候沒有很先進,我是頭幾個用粗線鋼絲這樣吊的,然後用電腦把它抹掉,以前香港拍武俠片很好笑的,弄個濾鏡上半部塗凡士林就這樣混過去,不打背光,所以每個鏡頭很短嘛,超過一秒鐘就看到那個線,所以那時候吊鋼絲是一個突破,有一個鏡頭是他們蜻蜓點水,那個時候剛開始可以做,做得不太好,現在看來也不及格。現在的話,當然可以做的東西很多,我們可以用合成,但是可能不受這個罪,有些東西拍不到,很有可能就沒有那個靈感,我記得拍完這個後去拍《綠巨人浩克》,到美國最先進做視效的大公司,他們都來問我你這個怎麼拍的,我就說這是吊鋼絲硬搞出來的,包括那些害怕的感覺都是真的。
電腦到現在很多輕巧的感覺都還是不太好弄,當然最後數位還是比較厲害,但做數位有個問題需要克服,因為大家知道有些東西你不可能實際拍攝,所以觀眾會比較放鬆。以前是特技演員去演,當時觀眾知道演出這個有多難會比較緊張,但現在知道數位可以做的時候,就不擔心了,刺激感、認同感會差一點。這要你發展出另外一種的認同感,我覺得大致來講技術進步是好事,當時那樣拍真的很危險,現在也不可能這樣拍,我後來才發現我對亞洲最大的明星周潤發做的事,在美國連特技替身都不能做,我把亞洲最大的明星吊在那,現在不可能讓你這樣弄,當然早期還有比我們更玩命的方法。古今中外各有各的拍法,除非你懷念以前的技術,像昆汀塔倫提諾說一定要怎麼樣拍,才有過去電影的影子。一般的話,盡量用不折騰人的新方法去試。
我覺得有一個新東西的時候,就有一種「純真感」,這很重要,你一定要突破那個方法,你做那些幾乎做不到的事情,有一種新鮮感、純真感,那是一種投入。我覺得電影一定要去挑戰這個,不挑戰就像鯊魚不前進一樣,就會死掉,不進則退。如果有一天我發現我沒有再突破,我就要退休,不必拍了,像這個有很多的挑戰,每次都是處子之身,我不會拍到第七部就油條了,因為我在拍一個我不會做的東西,那是一個挑戰,那個概念對我拍電影來說還蠻重要的,對我來說能挑戰很興奮。
Q:我之前看到一個採訪提到說,《臥虎藏龍》中有對演員按表操課,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東西,請導演分享,在拍片時候安排了什麼功課給演員?
李安:我常常拍片會下一些傻功夫,事後想有點傻,因為有一半的事情很傻氣。開拍以後,武術指導聽到後,給我一臉不以為然的表情,但也不好講我,那時候武打片很假,後來我拍了以後才知道,原來武打片不是武術,是舞蹈。用舞蹈的概念來做武打,我知道後很不服氣,如果我現在要拍的話,我還是要做這樣的東西。因為舞蹈與武打,舞蹈的力道跟真實的武打是相反的,我今天要把你摔過去,你會抵抗,我會用力摔你,但是電影裡我把你摔出去,是你讓我摔的,你要跳,物理是完全相反的,就是用相反的招數去達到你以為的樣子,那個就是武打片。
我讓他們去練真功夫,因為我覺得這樣才像,我覺得周潤發應該是練太極拳的樣子,不如就練練太極拳,這樣氣會比較沈穩,還有一些過去香港片我不太喜歡的動作,他們的動作非常不古典,都是武術指導搞出來的,他們做的大俠樣子我不喜歡,所以我要周潤發去調養氣質。章子怡當時不像玉嬌龍,我規定她要寫毛筆字,不是我要她毛筆字寫多好,坐有坐相、站有站相,小姐有要小姐的樣子,所以我要她練毛筆,這都是我自己想出的辦法,開拍其實都用不到,但對我來講,對他們來講,我覺得有些是有用的。而且現在的人跟古時候的人,基本上態度是非常不一樣,教養也很不一樣,周潤發的部分沒有問題,他演過很多戲,章子怡當時才十九歲,我當然要教她,以前的人不是這樣子的,我現在看很多拍我們那個年代的片,很多都不對,我們那時候不是這樣,但管不到了,我就管我還顧慮到的地方。
譬如湯唯演老上海戲,我覺得有一、兩個月調理一下是好的,我訓練湯唯穿旗袍走路,上海當時是孤島,抗戰的時候因為上海是租界,日本不能進去,很多人逃命到那個地方,久而久之有一套自己的文化體系和時尚,發展出一些很奇怪的東西,相當有意思。我們在拍那個時代,人體要跟著文化,湯唯外面穿風衣、裡面穿旗袍,既是間諜又是乖順的小女人,所以旗袍與風衣是很好的搭配,而且只有上海是這樣穿。風衣是講帥氣,走路要大步走才好看;旗袍是要小步走,因為旗袍窄,所以她的體態一個大步、一個小步怎麼走,所以就訓練這個步伐,從那個訓練可以啟發她原來以前的人是這個樣子的,像我國文老師或父母那代就是這樣教養,無形中對她的時代感會給很大的加分,這種是我很喜歡的訓練。她穿旗袍訓練,用橡皮筋把膝蓋綁住練習走一個月,接下來穿風衣大步要怎麼走,那些都是很好訓練。《色,戒》裡面有同學,以前的同學是怎麼樣?拿一些我們以前年輕看的書給她看,甚至讓他們打乒乓球也可以,就是要在一起相處。
我覺得這些訓練是好的,騎馬、基本的武術要練,武術有一個問題,她們都是學舞蹈出來的,舞蹈跟武術的力道是不一樣的,平劇、京劇、武行都是圓形的動作,很有力道,收腳坐臀整個是圓形的造型,她們學芭蕾舞蹈是伸展式的,沒有力道,你要把它變成圓形很難,後來一半都做不到,有一點點樣子就不錯。這方面你給楊紫瓊要求,她做得比較老道一點,她去找教練,從基本功踢踢腿開始練起,我覺得這是必要的,在這過程中你可以觀察演員的個性,很多演員軋戲、拍廣告,給你一個月檔期拍戲,我是不太相信這種做法,我覺得還是下點功夫好,尤其是拍古裝這種你不熟悉的東西。
我再放一段戲好了,這段我就不多講。最難拍的一個戲,用造水池、造新的方法、來拍最後情感的宣洩,其實是一個線性思考,也是看起來有Coverage,可是每顆鏡頭都非常非常的貴,你要申請經費,要透過片廠的核准,非常的困難。在台中造了個大水池,一般的水池就像洗澡盆一樣,水盪來盪去,我要做的是那種大海中波長很長的那種浪,所以要重新做水池,要做船的模型,還要做一個室內的深水池,把整個景沉到裡面去,然後加上很多很多的視效,我前面說我沒有當面跟父親道別,在這裡可以說道別,把我的情緒宣洩出來,對我來說這場戲很重要,這是一段大費周章,但跟故事沒有關係的一段戲,我覺得蠻值得放放看,看完之後看你們有沒有問題。通常如果你拍動作戲,片廠就會比較慷慨一點,動作戲一定是下音樂,但我的音樂是到最後最後才放出來,這對他們來講是很大的挑戰,我最後還是堅持下來,直到最後情感上來的時候才放音樂,那個音樂也比較特別,是一個英國少年唱詩班唱教堂的詩經,但是用印度梵文唱的,那個蠻特別的。(播放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船難片段)
這是我親身經歷一個很貴的經驗,你沒有辦法去看景、也沒辦法去模擬,不用動畫的方式就要不到錢,我花了一年的時間才要到錢,雖然這是投資公司找我拍的,我後來是用動畫,把整個水上的戲做出來,畫到一半大概四十多分鐘的時候拿到錢。我也沒做過動畫,我不是一個視覺訓練的導演,我是比較戲劇式的導演,是先看演員排戲後再決定怎麼拍,如果有畫面就去勘景,看到實物以後才在腦海形成一個畫面,如果完全沒有東西,要我憑空想像一個用視覺出發的編劇、構圖,那不是我的訓練,也不是我的長處和強項,但是為了這個我就必須要做,我有兩個主要的動畫師,他們有個團隊,十二年前要花蠻久的時間去做,現在做就很快了。先把動畫做出來再照著拍,我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憑空去想鏡頭角度,我可以想到特殊的東西,但很多東西在裡面就沒有辦法,所以我還是要一個工具Previs(預覽),用動畫把虛擬場景做出來,大船、小船、動物在哪裡?人怎麼樣?模型先造出來,我再去找他的位置,等於我在勘景,找到以後我再編排劇情,畫面做到差不多的時候申請預算。
我就直接用動畫Previs來做分鏡稿,分鏡完各個部門就可以討論怎麼拍,怎麼省錢、用什麼方法、可以籌備什麼東西,這些就可以開半年多的前製會議。我們還在台中造了一個水池,每天都在學習那個浪要怎麼造,後來那些浪還是不行,只能說跟船接觸的地方,船的動作感覺有點真實感,所有的水還是把它抹掉之後再畫。所以基本多數時候尤其是這麼大風浪的話,造浪池比較像一個平台,只是用水去動它會比用機器動真實一點,搞了很久,非常麻煩,視覺效果也做了一年多。這部電影還有很多3D上的發現,我覺得3D是另外一套學問,跟你腦中解析圖像怎麼運作,其實不太一樣,一般人好像以為3D就是2D加一個面象,但實際上差別很大,我們被訓練成對電影的理解就是2D的,但是3D其實要從中解放出來的,我拍到一半才瞭解3D有不同的面象,所以光怎麼打、戲怎麼演都不太對勁,那時候我的腦子還是2D的,我們並沒有經過3D的訓練。像風暴畫面都是純數位的就沒有問題,但如果是3D搭上實景去拍的,格數就不能做太多,動作不能太大,有很多的限制,那時候邊拍邊學。
Q:因為場景、對戲都是在虛擬環境,你是怎麼協助演員去拍戲?
李安:像這個小孩從來沒有拍過電影,他以為電影大概就是這樣子,我覺得人只要有想像力都不會是太大的問題,你演恐龍片看不到恐龍,靠想像去演,超級英雄片都是給他一個目標去假裝。比較複雜一點的就是與老虎打鬥的部分,這部分我們是先把老虎挑逗的動作拍出來,小孩是反過來演的,去偽造他讓老虎做出動作,對著銀幕反著做出來的。這種基本上是生存戲,像這場戲他要怎麼存活下來?靠本能,水沖過來沖過去,那都是很自然本能的反應,那都不是演戲。只有最後在喊sorry大哭的時候是演戲,那個我們放在平台上,這麼大的搖動其實是看不到臉的,我們當然要做點假的,讓他平順一點,然後鏡頭對準他,那個就很容易,我就跟他解說他在想什麼東西,那就是演戲,還是那個原則,動作大的不要講戲,很容易受傷,你就規劃好,要演戲的時候,你要讓他舒服地演、很安靜地演。
Q:導演有提到對於片名的發想有特別的理解,例如說《臥虎藏龍》是藏著慾望,導演對片名都很有想法,是創作的時候就有這樣去理解嗎?
李安:其實我大部分是改編人家的小說,原來就有書名,作者取這個書名是有些意思的,那我們要做怎麼樣的發揮,不是文字而是影像的,《臥虎藏龍》的「臥虎」是羅小虎,「藏龍」是玉嬌龍,書中沒有講這些道家的東西,我自己喜歡這些東西,書是很通俗的小說,一大段劇情都是我編出來的,我覺得就是因為道家的關係很有意思,可以做一個深層的發揮,不光是做一個武俠片。因為武俠片是一個比較野的片型,是一種guilty pleasure(罪惡的快感),是你心裡祕密喜歡離經叛道的東西,它有種野性在裡面,它釋放出兩千多年儒家教養的控制框架下的壓抑,你就是從這個離經叛道、不正經的事物去發揮。我拍《綠巨人浩克》就是暴力,它不明講,但存在美國國家中很深很重的暴力傾向,我們東方則是對性的壓抑,這是我的感覺。
我覺得《臥虎藏龍》就把這個主題給點出來,正好有這兩個女人的執著,李慕白就是個性貴氣的大俠,走路偏都不敢偏,其實李慕白受我影響比較多,在書裡面也沒有退休什麼的,都是我編出來的,玉嬌龍就是個大小姐,在小說是蠻可怕,有點反派的角色,我也加上我的想像。有些小說你要很尊重,有些裡面有些元素讓你可以借題發揮,我剛剛講那些都是自己想的,因為我覺得那是個禁忌的東西,我會很有興趣在武俠片拍出這樣的內容。
Q:請教導演是如何與編劇分工的,感覺《臥虎藏龍》有很大一部分是導演寫的,另外劇本寫到什麼程度可以開始勘景?
李安:《臥虎藏龍》主要是王蕙玲寫的,我覺得劇本是一個工具,像你會把舞台劇當文學來讀,沒有人會把電影劇本當文學來讀。電影劇本是一個藍圖、墊腳石,有劇本以後結構、初始的原意會清楚,真正創作還是在影像發揮,當然劇本很重要,它是骨架。我常常跟編劇合作都不是很愉快,因為我有很多想法,頭兩部電影自己編,是因為沒有人給我劇本,其實我是拍電影的,而不是作家,所以對我來講,編劇是蠻痛苦的一件事,常常寫不好。因為我的想像力是比較畫面性、戲劇性的,不太是在台詞與劇情的推演,而且現在主流電影的劇情推演非常的重要,這也是我不太喜歡的,所以跟有些有名的編劇相處不好,我要找聽我話的,但聽話的編劇在創意上又不太容易發揮,《少年Pi》的劇本我改到四百多稿就不算了嘛,我去勘景無時無刻不在想,一直在改,所以很難跟編劇相處。
如果是中文劇本的話,王蕙玲編出來的戲我看起來蠻好的,為美國工作人員翻成英文,他們看了會覺得奇怪,人家問你,答不出來也不太對勁,不是為了配合外國市場,而是真的講不通,你會發覺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,不管是英翻中、中翻英,只剩下本質的東西,你常會被文本給騙到,其實它的內容禁不起推敲,在改編過程中你會遇到這個問題,你看起來蠻順眼的東西,換成另外一個語言解釋不通,反之也是這樣。這一直都蠻令我頭大的,我有兩部電影是人家寫得差不多,我改了一些大致照著拍,其實那兩部我也不覺得劇本怎麼特別,可是都拿奧斯卡編劇獎,我拍的時候加很多東西,就像是給你們看《斷背山》的道別戲,劇本裡面沒有什麼就講分手就吐,你跟演員、場景、剪接創造出來的東西,很多惆悵的感覺也不是文字能傳達的。所以我覺得劇本是應該要好,但是我很怕劇本寫得很飽滿,那是片廠很喜歡的,如果劇本不小心遺失,誰拿起來都能導,能夠寫到這麼保險對片廠是最好的。
我覺得劇本應該是一個能夠發展拍片潛能的工具,這是我的感覺,我比較喜歡合作的編劇,他本身腦子不只是一個編劇,而是拍片的人,這種人合作起來會比較愉快,一起去想像這個世界、氣味。有些專門寫文字的寫得合情合理、工工整整的也可以,你們要再發揮就是了。我自己每次劇本都弄很久,寫一個劇本也寫好幾年,結果出手還是沒有把握,我都會參與得很深,不管是改編或無中生有,我剛剛說有些在現場寫劇本,是因為沒有辦法,現場沒有編劇,像是拍《色,戒》、《臥虎藏龍》,我在現場戲排不通,演員講不順口,或是吊在竹林上台詞不順要換成其他話,我只能現場寫,這也不是我很願意做的事情。


【結語】跟大家講話也是很有緣分,祝福你們都能拍到片,拍到心裡想要的片子。電影真的不是你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,所以要會想像、要會經營、也要會反應。我覺得電影會教你很多東西,所有工作人員都會教你,要有一顆開放的心,也要有主見,不然會亂,全憑運氣也沒有人天天過年。我覺得要有主見,激發你的想像力以後,收成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。我覺得是一個開放的心情,要有計畫,然後很多隨機應變。電影拍出來,人家要怎麼看就怎麼看,其實已經不是你的了。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裡面有一句我加的對白:「這個故事講給你聽,就是你的了」,我覺得電影也是一樣。別人看到這個故事以後,電影就是別人的了,也不是你的。那我們拍片的人,歸我們所有的就是我們拍片的經驗,去體驗跟你的夢想、跟你的團隊結合的那種生活經驗,那是可以帶回家存到你的記憶裡面的,那是你的生活體驗,這就是filmmaker。
所以拍片的時候要很珍惜,每個人都要很珍惜,在投入的時候你要確定每個人都很專心,不要有人在那邊鬼混,那是讓人非常生氣的事情。攝影機轉動的時候是非常寶貴,在之前跟之後很多的經營、很多的苦功,如果有一些能夠做到跟夢境有點接近就很值得。希望你們好運,能夠做到心裡想做的一些東西,跟你們的夢境有一些結合。也不要輕看基本功,你的craft(技藝)還是蠻重要的,藝術還是跟手上的技術有關係,真的手摸下去的觸感,所產生的化學效應,對我們來講那個就是電影。出來之後怎麼樣,是別人的事情,不是你可以去在意的。我希望你們能夠摸到想摸的東西,那個觸覺,真的手摸到的那個觸覺,是蠻寶貴的。雖然我們抱怨很多,可是我們都是幸運的人,能夠觸摸我們的夢想。
Good Luck Everybody!

